
(原書名:The Mephisto Club)
血液裡流動的邪惡,
是舉辦這場魔鬼盛宴的唯一理由。
橫掃歐美書市|電視影集全球熱映|美、英、德、法國人最愛的女法醫系列|
《貝納德的墮落》作者泰絲.格里森最新中譯本!
《史蒂芬.金談寫作》書單推薦作家,其著作為史蒂芬.金藏書必備
作品已譯成三十三國語言,全球銷量高達一千五百萬冊
惡魔存在,
而此刻他們正以殺戮來證明,
邪惡是如此真實……
【書籍簡介】
磁磚地板上有個大型紅圓圈,周圍有五灘等距、融化後又凝固的黑色蠟液。
正中央擺著被砍下的女性頭顱,眼睛直愣愣地盯著她們。
一個圓圈、五支黑蠟燭。這是場獻祭。
家家戶戶正歡慶聖誕的夜晚,珍.瑞卓利警探卻接到了一通破壞心情的電話──一起恐怖血腥的慘案發生,亟需她至現場處理。案發現場裡年輕女子身首異處,手臂被斬下,死狀淒慘,屋內還畫有召喚惡魔的神秘儀式,兇手甚至在餐桌上精心擺放了四份餐具。警方更發現,兇手行兇時,曾致電給一名與在場眾人熟識、專為歹徒辨護、被警方深惡痛絕的精神醫師喬伊絲.歐唐娜。瑞卓利警探不禁懷疑,歐唐娜醫師是否與兇嫌熟識。
數日後,歐唐娜醫師受邀參加一場神秘晚宴,在舉辦宴會的豪宅外,女警卡索維茲慘遭毒手,現場還留下另一名女子的斷臂,與門扉上赤色的倒十字圖案。死狀淒慘的屍體接連出現,顯然真的有某種令人恐懼的力量正在這座城市出沒。不久後,就連負責驗屍的法醫莫拉.艾爾思的家門前,也被畫上了記號……
這一切,是否和專與殺人犯打交道的歐唐娜醫師有所關連?
而兇嫌只是單純以殺人為樂,抑或這根本是一場魔鬼遊戲的前奏?
驚心動魄的分屍案件、召喚地獄的恐怖儀式、古老血脈傳承的人形惡魔──瑞卓利警探與艾爾思醫生這次要面對的,究竟是什麼?
PECCAVI 吾有罪
泰絲.格里森在《梅菲斯特俱樂部》表現出較以往不同的迷幻氛圍,從古老經典中發想的故事軸心帶來出乎意料的情節和閱讀樂趣,在某一瞬間彷彿真能看到惡魔躍然紙上。身為出色優秀的犯罪小說家,泰絲.格里森依舊設計了令人拍案叫絕的最終高潮,讓讀者緊張到最後一刻,掩卷後仍回味不已。
【作者簡介】泰絲.格里森 Tess Gerritsen 【醫學驚悚天后】

出生於加州聖地牙哥。母親是第一代華人移民,擁有華裔血統的她從小就喜歡窩在電影院看驚悚片,因而培養出她對黑暗主題的興趣,並反映在她後來撰寫的小說中。
泰絲畢業於名校史丹佛大學,而後繼續深造,最後取得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博士學位,於夏威夷檀香山展開她繁忙的內科醫師生涯。熱愛寫作的她,結婚生子後為了照顧兩個幼兒減少工作量,並開始嘗試寫作。
一九九五年對泰絲的寫作生涯是重要的轉捩點,在經紀人的鼓勵下,泰絲把自身的醫學背景寫進小說中,結果隔年出版的《貝納德的墮落》(Harvest)大受歡迎,讓「泰絲.格里森」這個名字首度躍居《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從此她專攻結合醫學和犯罪的醫學驚悚小說,迄今又出了十餘本書,本本暢銷,更創作出波士頓法醫莫拉.艾爾思和女警探珍.瑞卓利聯手辦案的系列小說。
然而伴隨著成名的後遺症來了,《貝納德的墮落》所描述的人體器官移植的黑市買賣,引發「美國器官移植協調人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ransplant Coordinators)的強烈反彈,這個組織嚴厲譴責小說中的情節,威嚇作者重寫不同的版本,並施壓派拉蒙公司不要將小說拍成電影,甚至反對格里森對『Harvest』的使用(『Harvest』一字在移植產業中,有器官移植之意)。然而泰絲卻對引發的眾多爭議不以為意。她表示︰「讀者要看醫學驚悚小說是因為他們想知道這個產業的內幕……我不是只想寫一個故事而已,我要讓讀者看到角色的內心,從中了解他們在乎什麼、害怕失去什麼。」
除了在紐約時報排行榜上獨領風騷以外,她的小說也是英國和德國小說排行榜的常客。她的小說《漂離的伊甸》不僅入圍愛倫坡獎及麥可維提獎,並且贏得了尼洛獎(Nero Award)的年度最佳推理小說殊榮;《The Surgeon》獲得瑞塔文學獎。媒體盛讚她的作品「心跳加快的閱讀樂趣」、「讓人提心吊膽的精采傑作」、「散文般精練的意境」、「令人心驚卻又獨闢蹊徑」,《出版人週刊》甚至封她為「醫學懸疑天后」(the medical suspense queen)。
二○一○年泰絲再創寫作生涯高峰,她的法醫莫拉.艾爾思和女警探珍.瑞卓利系列獲TNT電視台改編為影集,創下該台電視影集的最高收視紀錄,收視人口達七百六十萬,並引發熱情粉絲於網路進行同人創作。
泰絲目前全職寫作,與她的家人住在緬因州。
【哪裡買】
【延伸閱讀】
三輛巡邏車的藍色車燈一閃一閃地照著飄落的雪花,彷彿向來人宣示著:這裡出事了,而且事態嚴重。莫拉將車子擠到雪堆旁好留出空間讓其他車子通過時,她感覺到前保險桿擦過路上的結冰。今晚是聖誕夜,在這種時候唯一可能出現在這條小巷子裡的車,應該跟她一樣都是死神的隨從。閃爍的燈光照得她疲憊的雙眼直發昏。她強打起精神,準備應付接下來令人疲憊不堪的數個鐘頭。她的四肢麻木,血液循環的速度像是老牛拖車一般緩慢。清醒點,她心裡想,現在要上工了。
莫拉下了車,這時突然刮起一陣冷風,頓時吹散腦中的睡意。她踩踏在剛落下的粉狀細雪上,雪花像白羽般在靴子前飄散。儘管已經凌晨一點半,巷道旁幾戶不算大的住家依舊亮著燈。她看見在其中一扇貼有飛天麋鹿和糖果棒聖誕節蠟紙的窗戶後方人影晃動;一位好奇的鄰居正從溫暖的屋子向外窺探。今晚不再是什麼平安夜或聖善夜了。
「嘿,艾爾思醫生?」一名巡邏員警喊了一聲。她甚記不記得他的名字,但是對方顯然很清楚她的身分。這班警察都知道她是何方神聖。「妳今晚運氣怎麼這麼好啊?」
「彼此彼此,警官。」
「看樣子我們倆都抽中了下下籤啊。」他大笑一聲。「他媽的聖誕快樂。」
「瑞卓利警探在裡面嗎?」
「在啊,她和佛斯特一直在攝影存證。」他指著一棟燈火通明的屋子。這棟方正如箱的小房子夾在一整排老舊的建築裡。「現在他們大概都準備好,就等妳過去了。」
一陣激烈的作嘔聲音,引得莫拉往街道看了一眼。一名金髮女子正彎腰朝著雪堆嘔吐;她用手緊緊抓著長外套,以免下襬沾上穢物。
巡邏員警哼了一聲,壓著嗓子對莫拉說:「那個小妞將來可會是個厲害的重案組警探呢。她以為自己在演《美國警花》,大搖大擺地來到現場,對我們頤指氣使的。是啊,真是個驃悍的警花。才進屋子看了一眼,就馬上衝出來在雪堆吐個不停。」他哈哈大笑。
「我以前沒有見過她。她是重案組的人?」
「聽說她剛從掃毒組調過來。都是局長的好主意,說要增加更多女性探員。」他搖搖頭。「我敢說她待不了多久。」
這位女警探擦擦嘴,腳步虛浮地往門階走去,然後癱坐在階梯上。
「嘿,警探!」巡邏員警喊了一聲。「麻煩妳離開犯罪現場好嗎?如果妳還要吐,至少挑個沒有人蒐證的地方吧。」
站在一旁的年輕警察不禁竊笑。
這位金髮警探突然站起身,閃爍不停的巡邏車燈光映照出她喪氣的臉。「我想我還是到車上坐一會兒吧。」她喃喃地說。
「沒錯。去吧,女士。」
莫拉看著這位警探躲回自己的車子,不禁納悶自己將在那棟房子裡看到多麼可怕的景象。
「醫生。」巴瑞‧佛斯特警探呼喚道。他剛從房子裡出來,整個人裹在風衣裡,瑟縮地站在門廊上。他的金髮蓬亂,一副剛起床的樣子。儘管他的臉看起來總是呈現蠟黃色,門廊上的燈光讓他的臉色顯得比平常更加難看。
「我想裡面的情況應該很糟糕吧。」
「不是那種妳會想在聖誕節看到的畫面。我想我還是出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比較好。」
莫拉在階梯底下駐足,發現積雪的門廊上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腳印。「可以從這裡走進去嗎?」
「可以。那些全都是波士頓警局的人留下的腳印。」
「有沒有找到嫌犯的鞋印?」
「裡頭沒有太多發現。」
「怎麼,他是從窗戶飛進去的?」
「看樣子他離開的時候把腳印掃掉了。還可以看得到掃帚的痕跡。」
她皺皺眉頭。「這個歹徒很細心。」
「進去看了以後妳就知道了。」
莫拉走上階梯,戴上鞋套和手套。佛斯特面容憔悴,氣色從近距離看起來比剛才還差,一點血色也沒有。不過他深呼吸一口氣,勇敢地主動表示:「我可以陪妳進去。」
「不用了,你在這裡慢慢透透氣吧。瑞卓利可以帶我勘查現場。」
他點點頭,但是眼睛沒有看著莫拉。他的眼神眺望大街遠處,極力不讓晚餐反嘔出來。她留下佛斯特繼續跟自己的胃奮鬥,伸手準備開門。她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幾分鐘之前,她一身疲憊地抵達現場,試著保持清醒;現在她可以感覺到緊張的情緒猶如靜電,在全身上下的神經裡嘶嘶竄流。
莫拉踏進屋內,然後站在原地。她心跳加速,看著眼前表面上沒有什麼異狀的景象。玄關的橡木地板刮壞了。她從門口可以看到客廳,裡面擺著不成套的廉價傢俱──凹陷的沙發床、懶骨頭休閒椅,以及用木纖板和一塊塊混凝土搭組而成的書架。到目前為止,這裡不算是個那麼嚇人的犯罪現場。恐怖的景象還沒出現。她知道真正恐怖的場景一定還在屋子裡的某個地方等著,因為她從巴瑞‧佛斯特的眼神中和那位女警探蒼白的臉上看見了驚恐。
莫拉穿過客廳,來到餐廳,看到松木餐桌周圍擺了四張椅子。不過她留意的不是傢俱,而是擺在桌上、像是為一家人用餐而準備的餐具──一頓四個人的晚餐。
其中一個盤子上面蓋著亞麻布餐巾,餐巾沾有血跡。
她小心翼翼地伸手掀起餐巾的一角,看見盤子上的東西,然後手立刻一鬆,倒抽一口氣,踉蹌地往後退。
「看樣子妳發現左手了。」一個聲音說。
莫拉轉過身。「妳把我給嚇死了。」
「想看看真正嚇人的東西嗎?」珍‧瑞卓利警探說,「跟我來吧。」她轉身領著莫拉穿過走廊。
和佛斯特一樣,珍看起來也像剛從床上爬起來的樣子。她穿著皺巴巴的寬褲子,烏黑的頭髮糾結。不過與佛斯特不同的是,她毫無畏懼地移動著,罩著紙套的鞋子迅速踏過地板。有些警探固定會出現在解剖室,其中就屬珍最有可能直接湊到解剖檯前,俯身仔細觀看屍體。現在她沒有半點猶豫的神情在走在走廊上,反而是莫拉落在後方,仔細打量著地上的血跡。
「要靠著這邊走。」珍說,「這裡有一些模糊的腳印,兩個方向都有。是運動鞋。血跡現在差不多乾了,但是我不想弄糊任何一個印子。」
「是誰打電話報案的?」
「午夜之後有人透過九一一報警。」
「電話從哪裡打出來的?」
「就是從這棟房子。」
莫拉皺起眉頭。「是死者嗎?她試圖求助?」
「電話接通之後沒有任何人說話。報警的人撥電話到緊急事故中心後,一直沒把電話掛上。過了十分鐘,第一輛巡邏車趕到,員警發現大門沒鎖;一走進臥室,就嚇出了半條命。」珍在臥房門口停下來,帶著警告的表情回頭看了莫拉一眼。「就是這兒了,讓人看了毛骨悚然。」
砍斷的手就已經夠嚇人了。
珍退到一旁,讓莫拉仔細看看臥房裡的情況。她沒看到死者;視線所觸及的只是鮮血。人體內的鮮血平均約是五公升,用等量的紅色油漆潑在小房間裡,可以涵蓋整個房間。莫拉從門口探頭進去,驚愕的雙眼所見到的正是這樣潑灑得鋪天蓋地的血跡,彷彿有人粗暴地揮動手臂,將鮮紅色的彩帶拋在白色的牆壁、傢俱和床單上。
「兇手割斷了動脈。」瑞卓利說。
莫拉只能默默地點點頭,目光隨著血跡噴灑的弧線移動,解讀著鮮紅的墨汁在這幾面牆壁上寫下的恐怖事蹟。就讀醫學院四年級的時候,她輪調到急診室實習,曾經親眼目睹一名槍傷的傷者躺在創傷手術檯上大量失血。由於血壓急速下降,外科住院醫師在情急之下實行了緊急剖腹手術,希望能藉此控制住內出血的情況。他劃開傷者的腹部,大量鮮血猶如噴泉般從斷裂的大動脈湧出,噴在醫生們的白袍與臉上。患者臨死前的最後幾秒鐘,他們用消毒過的毛巾抽吸和加壓止血,而莫拉的注意力全為那些鮮血所佔據。血的亮澤、血的腥味……她把手伸進打開的腹腔裡,握著牽開器,浸透醫師袍袖子的溫熱感就像泡澡一樣舒緩人心。
莫拉那天在開刀房裡已經見識過微弱的動脈血壓所能造成的驚人噴湧。現在,她盯著臥房的牆壁,鮮血再度抓住她的目光,記載著死者生前最後幾秒鐘的故事。兇手下第一刀的時候,死者的心臟還在跳動,所以仍舊能產生血壓。血液最先像掃射的機關槍一樣,以高弧線噴灑在床鋪上方的牆上。心臟搏動了幾次之後,弧線的高度開始下降。身體會試圖彌補下降的血壓,所以動脈壓縮,脈搏加速。身體隨著每一次的心跳將血液排出體外,加速本身的死亡。直到心臟停止跳動,血壓消失,鮮血便不再噴湧,只剩最後的一些血液便靜靜地滲流。這是莫拉所看到、紀錄在四面牆壁與這張床上的死亡過程。
然後,她不再凝視牆上潑濺的血跡,轉而盯著剛才差點遺漏的畫面。某個使她不由得毛骨悚然的東西。牆壁上用鮮血畫著三個倒十字。下面還有一連串的神秘符號。
「那是什麼意思?」莫拉輕聲問道。
「不知道。我們也在研究。」
莫拉無法將目光從牆上所寫的符號移開。她嚥了一口口水。「我們這回到底遇上了什麼事?」
「好戲還在後頭呢。」珍來到床鋪的另一邊,指指地板。「死者的遺體在這裡。應該說『大部分』都在這裡。」
莫拉繞過床舖才看見被害者。
她一絲不掛地仰躺在地上,大量失血使她的皮膚呈現雪花石膏般的顏色。莫拉突然想起她曾經造訪過大英博物館的一間展覽室,裡面展示著幾十尊破損的羅馬雕像;大理石經過數百年的風雨侵蝕,雕像的頭部破裂、手臂脫落,最後終於成了殘缺不全的無名軀幹。這就是她在地上所看到的景象。一具殘破的維納斯,沒有頭。
「看樣子她是在床上被殺的。」珍說,「這就是為什麼血會噴在那面牆和床墊上。接著兇手把她拖到地上,或許是因為需要堅硬的表面來完成肢解。」珍吸一口氣,把頭往旁邊一扭,彷彿忍耐驟然到了極限,再也不能多看這具屍體一眼。
「妳剛才說報案十分鐘之後,巡邏車才抵達。」
「沒錯。」
「這裡所發生的事──肢解屍體、砍掉頭部──所需的時間絕對超過十分鐘。」
「我們知道。所以我不認為是死者報的案。」
此時房外傳來腳步聲,兩人同時轉過頭,看見巴瑞‧佛斯特站在門口,似乎不願進來。
「犯罪現場鑑識小組到了。」
「叫他們進來吧。」珍頓了頓,「你的臉色看起來不太好。」
「大致上還可以。」
「卡索維茲怎麼樣了?她吐完了沒有?我們這裡需要人手幫忙。」
佛斯特搖搖頭。「她還坐在車子裡。我看她的胃還沒辦法承受這種場面。我去把現場鑑識小組叫來。」
「叫她有些骨氣好不好!」佛斯特離開時,珍自他背後喊著,「我最受不了女性讓我失望了,壞了我們所有人的名聲。」
莫拉回頭看著地上的軀幹。「妳有沒有找到──」
「剩下的屍體嗎?有啊。妳已經看到左手了。右手在浴缸裡。我想現在應該帶妳到廚房去看看。」
「廚房裡有什麼?」
「更多的驚喜。」珍舉步穿過房間,進入走廊。
莫拉轉身跟上,冷不防瞥見臥室的鏡子。鏡子裡的她,正用疲憊的眼睛看著自己,融雪弄塌了烏黑的頭髮。不過令她錯愕的不是自己的倒影。
「珍。妳看。」
「怎麼了?」
「鏡子裡的那些符號。」莫拉轉頭看看牆壁上的圖。「看出來了嗎?倒影!那些不是什麼符號,而是字母,要從鏡子裡才看得出來。」
珍看看牆壁,再看看鏡子。「那是一個字?」
「沒錯。拼出來是PECCAVI。」
珍搖搖頭。「就算反過來,我還是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這是拉丁文,珍。」
「意思是?」
「吾有罪。」
這兩個女人互看了半晌,接著珍笑了出來。「這可真是一個精彩的自白啊。你認為唸幾句『萬福馬利亞』就能洗刷這個罪嗎?」
「也許它指的對象不是兇手,而是死者。」她看著珍。「吾有罪。」
「懲罰……」珍說,「復仇……」
「這是個可能的動機。死者做了某件事激怒了兇手。她犯下惹他不悅的罪過。而這就是他要死者付出的代價。」
珍深呼吸一下。「我們進廚房去。」她領著莫拉穿過走廊,來到廚房門口。她停下來望著莫拉,莫拉站在門檻前,瞠目結舌。
磁磚地板上有個大型紅圓圈,像用是紅色粉筆畫出來的。圓圈的周圍有五灘等距、融化後又凝固的黑色蠟液。蠟燭,莫拉心想。圓圈的正中央擺著被砍下的女性頭顱,眼睛直愣愣地盯著她們。
一個圓圈、五支黑蠟燭。這是場獻祭。
「好啦,現在我應該要回家陪小女兒了。」珍說,「明天早上呢,我們會坐在聖誕樹旁邊拆禮物,假裝真的世界和平。但是我滿腦子會想的就是……那個玩意兒……瞪著我的樣子。他媽的聖誕快樂。」
莫拉嚥了嚥口水。「我們查出她的身分了嗎?」
「這個嘛,我還沒把她的朋友和鄰居拖進來認屍。嘿,你們認得廚房地板上的那個頭顱是誰的嗎?不過根據駕照上的照片看來,我想她叫做羅莉安‧塔克。今年二十八歲。棕髮,棕眼。」珍突然笑了出聲,「把身體的各個部分拼起來,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妳還查出哪些關於她的事?」
「我們在她的皮包裡找到了一張薪水支票的存根。她在科學博物館上班。還不知道她的職位是什麼,不過照這棟房子和傢俱看來──」珍朝餐廳瞄了一眼,「她應該沒賺多少錢。」
此時她們聽到說話聲,還有犯罪現場鑑識小組進屋時的腳步聲。珍立刻挺起腰桿,以一如往常的沉著迎接他們。這就是大家所知的那位泰山崩於前也不改色的瑞卓利警探。
「嘿,各位。」她對小心翼翼走進廚房的佛斯特和兩位男性刑事專家說,「這個案子可有意思了。」
「天哪。」一位刑事專家低聲說,「死者的其他部分在哪裡?」
「分散在好幾個房間裡。也許你會想先看看──」她噤聲,身子突然一震。
廚房流理臺上的電話響了起來。
距離電話最近的是佛斯特。「妳覺得要接嗎?」他看著瑞卓利問道。
「接。」
佛斯特用戴著手套的手謹慎地拿起話筒。「喂?喂?」過了一會兒,他又將電話掛上。「對方把電話掛了。」
「來電顯示的號碼是幾號?」
佛斯特按下通話紀錄的按鈕。「是波士頓的電話號碼。」
珍拿出手機,看看來電顯示號碼。「我回撥看看。」然後撥了號碼,站著等電話接通。「沒人接。」
「我查察看那個電話以前有沒有打來過。」佛斯特說。他回溯所有的通聯紀錄,查閱廚房電話的所有通訊紀錄。「好,這是打給911的報案電話,時間是凌晨十二點十分。」
「是歹徒,他在炫耀他的成果。」
「還有一通電話,在那之前打的,劍橋的號碼。」他抬起頭,「撥出時間是十二點零五分。」
「歹徒從這裡打了兩通電話出去?」
「如果真是歹徒打的話。」
珍盯著電話。「我們來想想看。當時他站在廚房裡,剛剛才殺人然後分屍,切下她的手掌、手臂,將她的頭擺放在這裡的地板上。為什麼要打電話給別人呢?他是不是想炫耀?還有他想打電話給誰?」
「查查看。」莫拉說。
珍再次拿起手機,這次撥的是劍橋的電話號碼。「電話通了。嗯,是答錄機接的。」她頓了頓,然後突然看向莫拉。「妳絕對想不到這是誰的號碼。」
「是誰?」
珍掛上電話,重新撥號。然後把手機遞給莫拉。
莫拉聽到電話響了四聲。接著答錄機接起電話,放了一段錄音。一個令她立即不寒而慄的熟悉聲音。
我是喬伊絲‧歐唐娜醫生。很抱歉現在不能接聽您的電話,請留言,我會盡快回電。
莫拉掛了電話,對上珍同樣錯愕的眼神。「為什麼兇手打電話給喬伊絲‧歐唐娜?」
「妳在開玩笑吧。」佛斯特說,「是她的號碼?」
「她是誰?」一位刑事專家問道。
珍看著他,「喬伊絲‧歐唐娜。」她說,「是個吸血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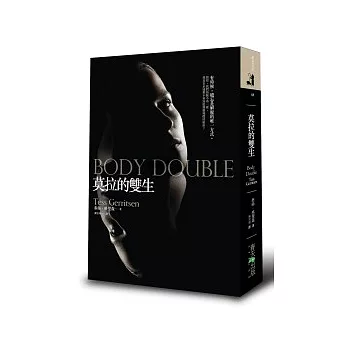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